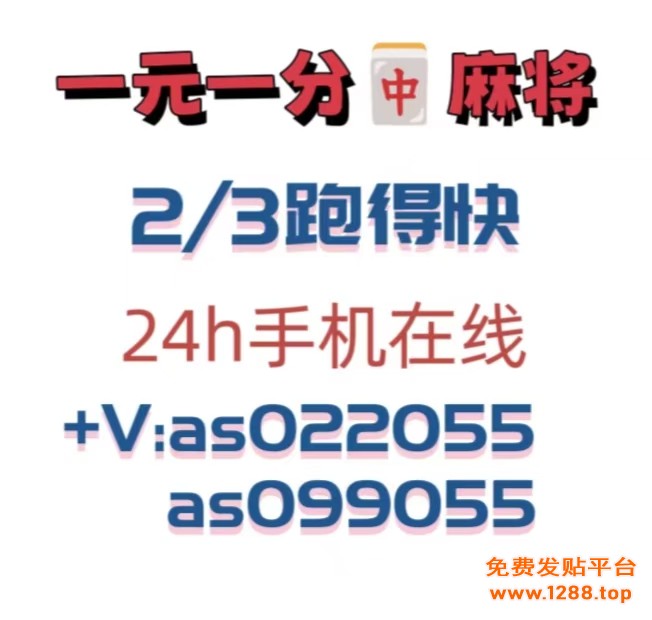
“妹妹呀,你最佳到猪栏里去看一看,那两只猪干什么如许喁喁叫的,大概由于没有吃饱罢,黄妈老是不肯给它们吃饱的
”八个月了,那年冬天,她底胃却起了变革:总是不想用饭,想吃陈腐的面,甘薯等
但甘薯或面吃了两餐,又不想吃,又想吃抄手,多吃又要呕
并且还想吃番瓜和青梅――这是六月里的货色,真怪僻,向何处去找呢?生员是领会在这个变革中所带来的预报了
他镇日地笑轻轻,能找到的货色,总忙着给她找来
他亲自给她到街上去买橘子,又托便人买了金柑来,他在廊沿下走来走去,口里念念有词的,不知说什么
他看她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妈磨过年的粉,但还没有磨了三升,就向她叫:“歇一歇罢,散工也罢磨的,年糕是大众要吃的
”
硕达无比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,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一起,你坠着我,我坠着你,往下沉
细水长流,咱们曾在一首歌里许下了本人的终身,在一首诗傍边写下恋情的篇章,如许的得心应手,要如许的倒霉之人,本领做到如许宽厚的相许呢?我想,我曾是佛前的掸子,纯洁着佛未知的身躯,佛便许给我,这终身的倒霉
/> 感觉黄海 前段时间与人闲说话,信口调了一句:散文是个筐,什么都能装
话虽粗俗,其实,细想,并不为过
散文走到今天,是英雄各显神通,你方唱罢我登场
写法不一,提法不一
早几年呼唤着学者散文,文化散文,其后是新散文
西安的黄海提出了原散文
用他自己的话说,原散文是原生态,生活本质的呈现
几个月前,有幸得黄海赠送他的新集子《秋天里的日常生活》
《秋天里的日常生活》从内容上,可分两部分
一部分是对下黄湾,这个村庄的怀念与触摸
收录了《下黄湾笔记》、《南部村庄》、《村庄1998年纪事》、《瓦屋记》、《昆虫记》等篇什
不管黄海自己是否承认,他对下黄湾这个南部村庄,更多地呈现了它淳朴、传统、落后、简单、随遇而安的一面,有着诗意的光芒
下黄湾构成了黄海的胎记
他用笔记录,也从这里出发
“我从下黄湾走过了,和一条土路或者一条细小的河流,一条通向远方的铁路一样,永不停息
《南部村庄》” 另一部分是黄海对在生活的城市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分解
鸡毛蒜皮、吃喝拉撒、个人简史,对于城市的细节
应该说这部分才真正体现了原散文中的原
物质是具体、真实的存在
细碎、繁琐中的物质、形态,实际上是抵抗着城市精神的废墟和灵魂的空洞
人生活在数字、地名、商品中,但这些东西对生活的添塞,也窒息着人心灵的通道
于写作而言,《秋天里的日常生活》一书,给笔者三点感受
一、独特 好文字,是有独特气息的
在日常地翻读中,见不少写手模仿时下颇为流行的一种写法
某几个论坛中,读十文如读一文,语气、节奏、用词、力度,乃至技巧皆为相同
例如某文中必有地名排列、必有时间简史
这种写法自某人起,大有蔓延之势
虽口不承认,看文字便知
以笔者愚见,虽是仿了写法、结构,却仿不了品质
这是根本的区别
黄海为文是从感觉出发的
他的文字没有太多技巧
是块璞玉,不事雕琢,自然天成
当前某几位写手写文是很细致地讲究构思、布局,巧合,写文或从上到下,从前到后,从内到外,把框架定上,然后抓住某点细致的描摹,依次填充,形成公文文字
写完之后,文章似乎大气恢宏,看过几篇之后,感觉却很疲累
语言的生硬、重复,多有乏味
黄海的独特在于他写作时的冷静和动笔前的感性
想写的冲动,让他无从考虑技巧的存在,所以他的文字有着独特的气息
可以整本书从头至尾读下来,绝无疲沓之感
大概源于这些文字是其心性的流淌,骨子里的自然
“味道“一次,是对他文章最好的注释
二、审美 时下,有众多的写手叫嚣着:服从内心
此种提法原是无可厚非,也符合人性
但怎样的提法都应该有个节制与规避
眼见一些人打着服从内心的口号进行肢体写作
下半身写作,不知道是先锋还是哗众取宠
笔者此言是有“假道德“的风险的
文以载道是速朽的,也很难达到
但社会责任感并非大而虚空
文学作为艺术的审美功能也不能丧失
散文写到今天,很难说哪种文章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模式
但是,有点责任感、干净一些,审美一些,我觉得对读者的心灵和眼睛都有好处
服从内心不一定与身体有关,也不必出现呻吟、潮湿、精液、等字眼
我想说得是黄海的文字是日常而物质化的,但其文章却给人审美的需求
他的文字让人的眼睛和心灵都干净
是一本可以放在孩子们面前去读的文字
读懂读不懂是一回事,能够放心地放在孩子们中间,这本身就是对个体写作成功与否最有力地证明与肯定
三、节制 黄海的散文有诗的特质,其语言格外干净,像是拿在阳光下晒过之后有了硬度
其中以《论颜色》一文最有代表性
语言的弹性给读者留下足够的空间
这些应该源自于黄海写文及为文的节制
节制使这个感性的人,在行文时呈现出冷静,色彩的冷处理,里面又有温情
正所谓:哀而不伤
节制使其文字碎而不烦
有些人的文字是繁复的
读时,让人感觉心浮气躁,难以淡定心情,进行从容沉静地阅读
眼睛一目十行,跳过内容,看结尾,或者结尾也忽略掉翻页而过
黄海的文字是冷静的
他几乎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,不急不徐地叙述,我在场又不在场
这是一种度的拿捏
笔者揣测这绝非是黄海刻意为之,而是他天赋使然
说到此,不得不感慨,黄海是有写作天赋的
文字如他口袋里的石子,被他率性地投掷,打上几个漂亮的水漂
前提是,在黄海玩心大起之时,那些文字的石子时常沉静在黄海的口袋中
相对于目前一些日日赶工的文字匠人,我更欣赏黄海的不玩
黄海在自己的文里说,他被城市这巨大的胃搅拌、浸染,渐渐失去了下黄湾青草的气息
我读他的文章时,有种强烈的感受,这种干净的青草的气息并没有失去,同时他的文字里面有着旁人欠缺的羞涩感
文品如人品,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偏颇,也能窥见一斑
祝福那个从下黄湾走出来的大男孩子,带着他独有的青草气息,和弥足珍贵的羞涩,继续写下更多更干净的文字
大哥与我的观点迥异,他反感父亲,倾向母亲,他的观点是,母亲没读书,没文化,遇事看不开,说话没深浅
相比之下父亲是强者,强者而不包容宽宥,有持强凌弱的嫌疑
大哥是母亲的靠山,母亲的自豪
他悲悯怜惜母亲,但我不知道怜悯能不能称作爱
就像疑惑孝道能不能称一样
爱在我们家,是一个陌生的字眼
